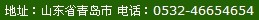|
△广告 左中美 异牟寻头戴莲花瓣纹双耳圆脸尖顶高冠,身着圆领左右带月牙形小领的袍服,端坐于龙椅之上。两手相向平放于腰前,手掌隐于袖中。腰部以下,袍服自然披开,从袍下左右突出的膝盖来看,乃为盘腿而坐,袍服线纹流畅,自然披向椅下。异牟寻所坐龙椅,两肩上所雕龙头形神可见,髭须分明。图上的异牟寻脸形饱满,神情沉静,目光平和。在他的左右,有手持藤杖的清平官,执扇侍者,目光皆朝向异牟寻。靠画面外侧左右,相向各坐一人,着汉官服,短翅璞头,据介绍,左者为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右者为异牟寻之汉师郑回。异牟寻座前正中,雕琢有一方莲花形云纹供案,供案由一坐僧以右手单手托举,桌上所置供品共三盏,坐僧盘腿于一云纹石座,其左手放于左膝之上。异牟寻座下基石前额,左右各刻有一朵莲花。在其身后石壁上,左右各刻有云纹及火焰纹图案。整幅画面雕刻于红砂石壁之上,使得画面所刻人物着上自然的红砂彩。画面外框为一拱门状,框上雕有一圈均匀的珠状纹饰。 初夏,上午的清朗阳光照着松林古柏间古老的石钟寺。云南,大理,剑川,石宝山,石钟寺,一早前来朝山的人们扶老携幼,络绎前来,来拜谒这清静的古寺灵山,且领略这满目的松风云意。在这些进山的人们中,有众多说着普通话的远道来客,想是初次前来踏访。而那些神情平和、看上去熟门熟路的当地人们,该是怀着拜佛谒祖的安详心意上山来的,上山,入寺,在那一尊尊熟悉的石窟壁刻前,再领一番佛的慈悲心意,再谒一回祖先的安详面容。石壁间,诸佛和先祖的古老目光里,一片大地的千年往事,悠远流淌。 石宝山石钟寺一号石窟,被名之为《异牟寻议政图》。异牟寻(-年),南诏始祖细奴罗第六代孙,其父凤伽异,生前为阳瓜州刺使,早逝。公元年,南诏第五代王阁逻凤去世,异牟寻即位,为南诏第六代王,至年在位,共在位三十年,为南诏重要的中兴之主,在其治理之下,南诏渐进入鼎盛时期。其时的南诏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女王国的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毗邻,西南和骠国(骠国的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治地包括以大厘城(今大理喜洲)为中心的十睑(赕)、六节度。其中,六节度为:弄栋(姚安县)、永昌(保山县)、银生(今景东县)、剑川(剑川县北)、拓东(南诏别都,今昆明市)、丽水(在腾冲县西),疆域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异牟寻仿效中原封“五岳”“四渎”,以彰南诏山河之壮阔,以望国家政基之久远。所封“五岳”分别为:中岳点苍山(今苍山),西岳高黎贡山,南岳蒙乐山(今无量山),东岳乌蒙山,北岳玉龙雪山;“四渎”为:金沙江,澜沧江,黑惠江,怒江。南诏域中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文化上,同时受汉唐文化、吐蕃文化影响。同时,因起始于汉代的古西南丝绸之路穿境而过,使得是时的南诏之地亦深受境内外多种文化的影响和濡染,由此形成了其文化上兼容并蓄的开放格局,并深深融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石钟寺一号窟《异牟寻议政图》共刻人物九尊,从画面所刻人物、服饰,都充分体现出了南诏文化内外兼融的多元性。 石宝山,当地白族语称为“走奔善”,意为“堆满大石头的山”,“石宝”一名最早见于明景泰元年(年)沙溪土官百户杨惠墓碑上,以“石相可宝”而得名。山上的丹霞地貌红砂岩龟背石独具特色。明《万历云南通志》言石宝山“有石佛、石栈、石人、石井、石伞、石象、石狮、石钟、石鼓之异,五色踯躅,被于陵谷。”山中开凿于唐、宋年间的石窟,分布在石钟寺、沙登箐、狮子关三地约六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17窟,造像尊,被誉为“西南之敦煌”。石刻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同于国内各大石窟雕刻,为佛教题材,中有佛、菩萨、观音、天王、明王、力士、胁侍、罗汉等。另一类为世俗题材,如南诏王议政图、清平官、醉酒汉、“阿央白”等。 世俗的君主作为主体被雕到石窟之中,这在全国各地历代以来的石窟雕刻中绝无仅有。石钟寺第二窟,名为《阁逻凤出行图》。阁逻凤(-),南诏第四代王皮逻阁之子,为南诏第五代王,至年在位,共在位三十年。南诏地处一隅,东有汉唐,北有吐蕃,为国之生存计,历代奉唐为尊。自始祖细奴逻起,多受大唐册封。阁逻凤执政期间,南诏迅速发展壮大,势力逐渐强盛。唐天宝九年(年),阁逻凤因路过云南太守府(姚安),太守张虔陀侮辱其同行的妇女,且勒索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派人辱骂之余,并向唐朝廷诬告其罪。阁逻凤愤怒起兵,攻破云南太守府,杀张虔陀并取羁縻州。天宝十年至十三年(—),唐两次起兵讨击南诏。在第二次天宝战争中,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南诏首都太和城,全军覆没。后阁逻凤在太和城中立“南诏德化碑”,碑文数千言,言明叛唐出于不得已,以碑明心,留于后世。 石窟《阁逻凤出行图》共刻人物16尊,阁逻凤头戴高冠居中端坐于龙椅,其左侧六人,分别握剑、执扇、执旗;右侧七人,六人亦分别握剑、执旗、执扇,中有一僧结跏趺坐,着袈裟,执念珠,据传为王弟阁陂和尚,其后有一人为其撑曲柄“杠伞”。靠近窟门处若一号窟雕两位清平官对坐。阁逻凤王座前,雕有蹲伏着的一狮一虎。左右握剑、执旗之武士筋肉突起,装束紧牢,显出强健有力之态。从画面上旌旗飘动、武士簇拥的场面,表现出画面所刻为阁逻凤出行坐朝的情景。 除石钟寺的两窟南诏王坐朝图,还有被名为《细奴逻全家福》的狮子关一号窟,窟中坐石上共雕刻五人,中戴高冠、蓄胡须者为南诏始祖细奴逻,旁边戴莲花冠者为王后,二人均面肤丰满。中间坐一小孩,左右两侧亦坐男女孩各一人,座后有屏障,绘红绿两色帐幔。此窟造像,充满人间生活的气息,为石窟雕刻艺术中所少见。 细奴逻,阁逻凤,异牟寻,三座以南诏极重要的三位诏王为主题的石窟造像,徐徐展开南诏兴起、壮大、中兴的历史画卷,一千多年前这片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滔滔往事,借着那些栩栩如生的石刻画面,扑面而来。 而在石钟寺一共八组石窟造像中,体量最大、人物数量最多的则为佛教造像。佛教在南诏国时期传入云南,以密宗为主,“唐宋间传至云南佛法不止一宗,而以阿吒力教为盛。阿吒力者,瑜伽秘密宗地,蒙(南诏)段(大理国)时期此教最盛。”《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研究称,南诏、大理国崇信的佛教有来自中原汉地、西部吐蕃以及南部印度等多种渠道,而其中通过古印度僧人经南方丝路传入的密宗阿吒力教派影响最大。石钟寺三号窟到七号窟,皆为佛教人物造像,第五窟《愁面观音》图,其间点缀着樵夫、老翁、琴师、童子等世俗人物,观音身体前倾,凝视人间。 从南诏至后来的大理国,多年的时光里,佛教成为境内影响最深、最广的宗教,佛教的影响,深深融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石钟寺一号窟《异牟寻议政图》,画面内容呈现为议政,而异牟寻头上的莲花纹高冠、座下基石上的莲花刻,其盘腿而坐的姿势,以及座前托案的坐僧雕刻,无不彰显出其中的佛教雕刻元素。为此,在一些研究资料里,又把此图名为《异牟寻礼佛图》。 纵观石宝山灿烂的石窟雕刻,可谓刻在石壁上的南诏历史画卷。石钟寺、沙登箐、狮子关三个点共17窟、尊造像,外加碑碣五通,造像题记和其他题记四十四则,几乎全面反映了是时南诏的政治、文化、对外交往乃至民间的风俗民情,各种宗教和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影响最广的佛教在当地的传播中,又悄然融入了当地民族的本土文化元素。比如石钟寺七号窟的“甘露观音”造像,体态丰盈,双肩圆润,其躯体显出当地白族妇女的特征,而其精美的耳饰、臂钏、手镯却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营养,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狮子关二号窟的梵僧造像“酒醉鬼”,三号窟的“波斯国人”,其深目高鼻的形象和衣着服饰特征都印证了当时的南诏古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印缅、西亚地区密切的宗教文化以及经济交往。 应该说,古代石窟艺术在云南并不发达,而在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石窟雕刻艺术。石宝山石窟雕刻,在吸收了此前中原地区魏、晋、隋、唐石刻艺术风格的同时,融入地方民族文化,成为独具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独特石窟艺术珍品。促成此石窟艺术瑰宝的原因,一为南诏地处中原与南亚、西亚连通的交通要冲,穿境而过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时带来了古老的中原文明和境外文明,使得南诏虽地处一隅而广见识。二为南诏之境,历来民族众多,又兼西接吐蕃、连西亚,南接缅越、通古印度,东则深受中原灿烂的汉文化影响,由此,形成了南诏文化兼收并蓄、多元并包的开放格局。其三,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则是剑川之境,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经三次发掘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研究表明,在距今约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土著先民在此生活。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是目前云南已发掘的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剑川因此被誉为云南文化之源。历史上,剑川是云南著名的三个“文献名邦”(大理、剑川、建水)之一,历史文化深厚,且域中历来多善刻之人,故此而成就了石宝山珍贵的精美石窟雕刻群。 因汉人权臣郑买嗣于公元年突起灭国,除了《南诏德化碑》《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外,相对来说,南诏多年历史留给后世的资料并不详细,尤其是南诏王陵所在,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此背景之下,剑川石宝山石窟群,凭着石刻这一可存之久远的艺术形式,使得人们可以在其间,重新解读一千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那一段悠远往事。 望山下,五月的剑川大地,豆麦渐收,勤劳的人们就要播种下又一轮的大春作物 ——有若,千年前某一个艳阳初炽的夏天。 来源:云南日报 △广告△广告赞赏 长按北京中医白癜风医学研究院怎么样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医院效果好
|
当前位置: 剑川县 >闲情剑川石窟解读刻在大地上的千年往事
时间:2017-11-1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要闻直播省公安厅督导组深入剑川调研督
- 下一篇文章: 剑川神快来帮忙,这三名剑川学生要上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