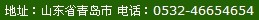|
走进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研三学生曹豆豆的实验室,不同形状的“颅骨”“肋骨”“肢骨”“牙齿”等样本有序地摆放在桌面上。 “这个颅骨精致小巧,额头光滑有型,是一位女性个体的。这个颅骨更加粗犷,额头也更加倾斜,是一位男性个体的……” 曹豆豆细致地向大川介绍着她日常打交道的“伙伴们”,神态轻松。 “会觉得害怕吗?” “不会,他们是我的研究对象,也是几千年前的先辈,我很尊重他们。”她随意将过肩长发别在耳后,笑容干净。 这样的问题,曹豆豆见多了。整天与人类骨骼打交道,她的经历令不少人好奇。 扬帆:感谢“引路人” 曹豆豆还记得,在李永宪老师的“考古学导论”课堂上,她开始对考古学产生兴趣。 总是提前十分钟到教室、衣服永远熨得笔直整齐,曹豆豆口中的“大李老师”是年过六旬的考古学家,他帮助曹豆豆推开了考古研究的“探险之门”。 “考古最开始就是探险家的故事,后来成为田野与文物研究的一个学科,大李老师阅历丰富,讲述的世界博物馆等很多知识,都让我向往不已。”曹豆豆说。 大一下学期专业分流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考古学。 这颗好奇的种子,在大三上学期的田野实习中破土而出。 十月的云贵高原,秋风入骨。在大理市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实习的日子里,大家中午穿短袖,晚上裹羽绒服。从老师到学生,一行四十来人挤在一栋租来的二层小楼里,一间房分上下铺,住六到八人。 △曹豆豆和同学们在整理发掘出的陶片等遗物 早上8点“上工”、晚上11点倒床就睡,曹豆豆记忆中的那段日子,累却快乐,也真正理解了田野考古。 “探方都是不能踩的,踩了就友尽。”曹豆豆笑着说起当时的玩笑话。她从自己负责的两个探方里发掘出了铜钱、石箭镞、牛角、玉器等遗物。 △气候潮湿,发掘出的陶片上长出了绿植 三个月的实习经历虽辛苦,却坚定了曹豆豆继续做科研的想法。“我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但是去田野让我感觉很特别,既能动手实操,又能安静地思考问题。”曹豆豆笑道,“或许是因为那段日子太难忘了。” “从喜欢上考古,到想继续做科研,这一切都顺其自然。”这个过程中,她特别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各位老师,“感谢‘引路人’们,让我了解到自己所学的乐趣与意义”。 △曹豆豆(左二)在考古工地上 起航:“挑骨头”挑出了专业方向 田野实习返校后,曹豆豆努力为读研做准备。喜欢淘些“破铜烂铁”的父亲很支持她继续深造,并建议她选择陶瓷、青铜器之类“更出彩”的研究方向。此时的曹豆豆没想到,自己会和人类骨骼打起了交道。 大三下学期,曹豆豆在原海兵老师的“体质人类学”课堂上,了解到人类骨骼的考古和科研价值。“当时我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山遗址的人类龋齿很感兴趣,觉得可以做一些研究。” 于是,她参与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山遗址人类骨骼的清洗、分类和挑拣工作中。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清洗人类颅骨的场景。“因为颅骨里面有很多土,洗的时候就要给它掏土,当时还觉得有点怵,觉得像在‘掏人的脑袋’。” △曹豆豆用于整理的部分工具 但曹豆豆没有放弃。一方面这项工作本身的学术背景,她本人对此并无忌讳,“只是一些研究样本,是必须的环节”。另一方面,支撑她前行的是原海兵老师的信任,“很感谢原老师,愿意把这件重要的事情,交给什么都不懂的我来做,我觉得我就要做好,不能辜负老师”。 早上7点半到实验室“挑骨头”,晚上10点钟保安敲门再离开,曹豆豆花了两周的时间快速地完成了人骨挑拣工作。分不清各部位的骨骼就翻书找,书上找不到就把问题记下来问老师,就这样一点一滴,曹豆豆慢慢摸到了“门道”,从这堆骨头中挑出了81例人类个体的牙齿,累计颗。 接下来的一个月,曹豆豆一直在“看牙”。牙齿是人类身体中最坚硬的部分,“就像有老师打过的比喻,‘每颗牙齿在我眼里就像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这期间,大部分时候只有她一个人与研究样本相对,“为防止自闭,我还买了一个蓝牙音箱陪自己说话”。 后来,这些材料在整理完善后,成了曹豆豆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资料来源。 △曹豆豆(左二)本科毕业留影 也因这段经历,曹豆豆顺利保研本校后,跟着原海兵老师继续着体质人类学方向的研究。 破浪:骨骼是古人的墓志铭 在海门口实习期间,因为长时间跪在地上“刨土”,曹豆豆的膝盖至今仍时不时隐隐作痛。“应该是进了‘湿气’,当时很傻,没有采取治疗措施,天气一冷就会痛,夏天不敢穿未过膝的裙子,冬天还会戴护膝。”从那以后,曹豆豆说自己更加注重在田野工作时自我保护。 自剑川海门口遗址至今,曹豆豆又先后9次下田野。 而山西汾阳的“下墓”经历,则是一次与自己内心恐惧的博弈。那时她刚上研一,面对六、七米高的墓壁,有点恐高的她生了退意。“就算是踩着梯子下去,一开始也是头晕眼花,感觉腿都软了。” 原海兵老师照顾她,有意不让她下墓,老师自己却身体力行下到墓底,专注地做现场记录。“真的很辛苦,脑力体力都要消耗,尤其是出墓的时候比较费劲,因为墓比较深,几天下来要看上百座墓,每一天结束时都累极了。” 曹豆豆不想退缩,硬着头皮下了墓。 接下来的一幕令她汗毛竖立:白森森的颅骨上,一只只黑色的虫子从眼眶中钻出来,又爬进鼻孔里。 “那时候去田野不多,其实有点怕,感觉像极了电影木乃伊中的惊悚画面。”但她还要现场记录下性别年龄,并检查颅骨和观察牙齿,“看着虫子从我手边爬过,习惯后觉得自己胆子也变大了。” “我相信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曹豆豆这样形容她的一次次田野经历。“能下田野就要下田野。考古系的学生只埋头读书、实验而不去看田野信息,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些年,曹豆豆也遇到过一些对考古学的误解,她说考古学是一门严谨且科学的学科,和学校里其他专业一样。“通过学习,我们只会更加清晰地还原古代人类社会,消除大家的误会。更没有‘害怕’一说啦。” △曹豆豆(右)在考古工地 日常生活里,曹豆豆喜欢戴一枚牙齿形状的胸针。在众多人类骨骼中,她最喜欢也最熟悉的,是牙齿。“我们专业有句话叫‘透骨见人’,骨骼不会说谎,我们带着想象和情怀,根据历史和文化,通过骨骼去复原古人的一生,就好像在与他们对话。” △曹豆豆的“牙齿”胸针 “古人的骨骼就是他们的墓志铭,而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释读出铭文’,让无声的历史变成有声的故事”。 在历史文化学院三楼的考古实验室里,曹豆豆用双手书写着属于前人的历史。就在此时,就在此刻。 来源:四川大学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chuanzx.com/jcfc/15273.html |
当前位置: 剑川县 >让无声的历史变成有声的故事与人类骨骼为
时间:2023/3/1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大理除了风花雪月外,街街流水,户户
- 下一篇文章: 国家的保护植物云裳仙子大理百合花